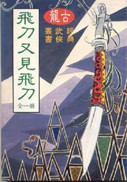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文章资讯 >>本章试析古龙作品中的“大丈夫”人格理想:古龙小说全集阅读
此文首发于《华文文学》(2001年/2期),作者马骏。本文由青龙于2007年1月17日录入并整理上传,热血古龙(http://www.rxgl.net)首发于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与原作者名!谢谢。
古龙小说
古龙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异军突起,自成一家并广为流传,是与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分不开的。他本着“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宗旨,对于人性给予了特的关注与描绘,将写人、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与性格这一文学命题应用到武侠小说中来,从而刻画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文学是人学,本文将力图分析通过古龙成熟时期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大丈夫”人格理想。
古龙曾多次说过:“武侠小说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应该开始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古龙之所以要这么做,恐怕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与古龙自身的经历有关。他大量地接触到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潮,同时他自己对人生也有很多体验与感悟,他通过小说把这些思想表达了出来;第二,武侠小说自身发展的需要。古龙认为武侠小说也应在文学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因此需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不断创新;第三,受当时台湾的文艺政策影响。1965年4月2日至8日台湾军队当局召开了军队第一届文艺大会,提出以进步的人文主义去替代落伍的“战斗文艺”的口号,认为人是一切的根本,新文艺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提高人性的尊严,谋求人群的幸福。②正因为如此,古龙将他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情感和人性的冲突。
古龙已经意识到了人性中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种尖锐痛苦的矛盾。“其实每个人都有两种面目,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否则他非但无法做大事,简直连活都活不下去。”(《萧十一郎》)因此,古龙笔下的很多人物的行为处世只是发自于人类的情感和人性的冲突,他们亦正亦邪,是“正中带有三分邪,邪中更有七分正”,他们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时还有些失误,可以说古龙写的不是“好人”也不是“圣人”,而是“大丈夫”。尽管古龙古龙小说全集的小说通常缺乏历史感,只是在一个横截面上去展开描写,从而使得“大丈夫”的性格基本上缺乏发展,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总归他写的是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活生生”的“大丈夫”,而不是以往经常出现的那种高大全的“圣人”,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是古龙乃至人类内心深处期待和向往的某种理想人格的化身。
那么这种“大丈夫”人格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孤独感。让我们首先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古龙笔下的“大丈夫”多为一些游荡江湖浪迹天涯的浪子。尤其是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世来历全都是个谜,最多说明是个孤儿而已。他们没有家,没有门派,也少有知己。他们无依无靠,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何处去,如同无根的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孤独地面对人生的种种冲突和选择,给人一种萧索沧桑之感。如萧十一郎、傅红雪、阿飞、小方等。在这无边无际的天涯孤旅中,尽管他们也觉得累,却从不敢休息,因为人生就像鞭子不停地在后面把他们向前赶,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③从而磨砺出他们的“大丈夫”人格。此时不时占据他们心头的,就是孤独和寂寞了。
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多深的痛苦和烦恼,都比不上‘寂寞’那么难以忍受。这里纵然有最美的花朵,最鲜甜的果子,最清凉的泉水,却也填不满一个人心里的空虚和寂寞。”(《萧十一郎》)因此,尽管萧十一郎明知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让他觉得痛苦、厌烦,但每当他在这美丽而纯净的山谷中呆上一、两个月后,却还是要走出山谷去外面闯荡一番,以排除心中的孤寂。虽然这样,这些“大丈夫”却仍要以极大的勇气来面对孤寂、选择孤寂,因为他们不是世俗中的普通人,而是“大丈夫”。一方面,他们是高手,不仅武功高,还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格,是“高处不胜寒”,他们的武功境界、人生境界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他们的处世原则也是别人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孤独。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也正在于此。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需要孤独,他们要在孤独中成全并保持自己——保持自己生命的完善、理想的纯洁、个性的张扬以及人格的独立,因为这些注古龙武侠小说定了只有在孤独寂寞困苦之中才能实现,尤其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的第一个前提是孤独意识。没有意识到人有孤独的权力的人,也就没有意识到人格。”④因为人格(Personality)的本义就是面具(Mask),其首要含义即是指个人性或私人性,它注定了属于独立的(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孤立的)个体,若否定了个人的独立性也就否定了人格本身(在这里人格与道德并非是等同的关系)。正因为这个原因,“大丈夫”不仅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而且还对这种孤独感给以自我肯定并视为需要。因比,“大丈夫”自己选择了飘泊,选择了孤独。《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抛弃了官职,把一座豪华庄园及恋人送给了龙啸云,孤身一人出关而去。《三少爷的剑》中的谢晓峰宁愿流落街头,帮人挑粪、喂马,也不回神剑山庄做“三少爷”。正如萧十一郎所说的那样:“但一个若要活下去,就得忍耐……忍受孤独,忍受寂寞……只有从忍耐中去寻得快乐。”如果一个人忍受不了这些,他是不会成就自己的理想,也就算不上是 “大丈夫”了。尼采不也是认为孤独实在是一件美德,是对高洁的渴望和追求吗?一个人只有有意识地与周围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随波逐流,他才能明察本心,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存在,意识到我之为“我”的独特性、唯一性,从而建构起自己独立的人格。
正是由于“大丈夫”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建构了他独立的人格意识,从而树立了他的责任感。“真正的责任心蕴藏在孤独意识本身之中,那些尚未把自己与别人、与群体区分开来的人,那些还在群体襁褓中昏睡不醒的人,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责任心。”⑤当然,这里的责任感并不是那种大而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虚幻的“责任感”,而是直接地为自己负责从而间接地为他人负责。“大丈夫”清楚地意识到,我就是我,既然我是与众不同,既然我的所做所为都是出自我独立自主的选择,那么由我的行动所带来的任何后果都必须由我独自一人来承担而不能推托。“是自己做错的事,自己就要有勇气承担。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必推诱责任,就算错得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多,也不必学泼妇骂街,乞丐告地状,到处去向人解释。”(《大地飞鹰》)《绝代双骄》中那个外表玩世不恭但却心地仁厚的小鱼儿,在被慕容九追杀,实在逃不掉之际突然引发小孩子的童心,装鬼把慕容九吓昏过去,才得以逃脱。事后当他得知慕容九因此精神失常,流落街头,随时有被人欺侮的可能时,却又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她恢复正常并送回家,才能将自己的这段心事了却。在这里,“大丈夫”意识到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外在的义务,更是自己内在的权利,是二者的统一。
“大丈夫”的独立人格不能不包括尊严在内。人的尊严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面子”或“身份”,而是指“人内心对自己精神主体的自觉坚持”。⑥它首先涉及到自尊,并在自尊的基础之上同样去尊重他人。因为真正的自尊是以承认人人都有独立而平等的人格为前提,是对这种普遍性的尊重。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古龙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即是指他对于人的人格、尊严、利益和个性的关注、热爱和尊重。他笔下的“大丈夫”平时是十分随和浪漫的,颇有些玩世不恭之意,但一涉及到上述这些方面时,却又变得十分的严肃认真。他们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一贯的原则,不容许他人来侵犯,甚至不惜为些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所谓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⑦同时,“大丈夫”也承认他人的尊严并尊重他人作为人的人格、权利而不论男女老少,是何身份。如在《楚留香传奇》中有一个人残酷地打碎一个被挖去双眼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洞窟里受人玩弄的妓女的仅存的希望时,一向极少出手的楚留香愤怒地出手了。因为楚留香知道,她们是人,只要是人,就是平等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别人的尊严和生命。古龙小说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还在于 “大丈夫”对于他真正的对手的尊重和理解,他为能拥有这样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而骄傲,因为这些对手在某些方面也同样可称为“大丈夫”,至少不是小人。古龙就写出了很多这样关系微妙,在决战在即生死牧关之际仍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的对手,如谢晓峰与燕十三,李寻欢与郭嵩阳等。当谢晓峰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际,即将与他进行生死决斗的燕十三却乔装打扮赶来为他医治。而郭嵩阳为了给李寻欢试探敌情,甚至不惜以身试剑,硬是用身体去接对手的剑,结果留下一具有十九处剑伤的尸体让李寻欢研究敌手的剑法。
提到了对手,就不得不提及朋友了。
第二,重友情。古龙的 “大丈夫”虽然孤寂,但并非完全与他人绝缘,他们孤寂但不孤绝,孤独但不孤僻,相反,他们的孤寂正成为他们真挚友情的坚实基础。正因为孤寂难以忍受,所以 “大丈夫”有着比普通人对于情感交流的更强烈的需要,希望以此来填被心灵的空虚,抚慰浪子的情怀。“孤独与排除孤独是人生的两大需要。”⑧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对于友情的热烈赞颂乃是古龙武侠小说的又一大特色。其它一些武侠小说也写过一些所谓“朋友”,然而这些朋友之间的情义却多是有着其他一些社会因素来维系的,如师门关系、道义关系、利益关系等。即使有一些投缘的也多半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离开“朋友之地”而结拜成 “兄弟之境”了,如郭靖、杨过等人与老顽童的忘年之交。然而古龙笔下的“大丈夫”之间却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独立而平等的人格之上的真正的友情,他们的相交完全出自于内心真诚的情感流露而不受任何外在世俗因素的影响。尽管古龙有时也有怀疑,认为你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你潜在的最大敌人,但同时他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对手也是最能理解你的人。因为能有资格成为真正对手的两人之间,多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能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对手毕竟不等于仇敌,并不是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而只是要通过过招来肯定 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无论是重视友情还是尊重对手,其实质就在于对理解与交流的渴望。试想两个独立的灵魂在各自的轨道上孤寂地运行着,若能有缘相互碰撞而交织出耀眼的火花将是何等的幸事!“大丈夫”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对于他们来说也就足够了。因为友情,他们可以分享快乐,分担忧愁,可以一诺千金,赴汤蹈火,但他们自己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伟大或相互恩欠,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超功利的情感关系,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沟通,这是一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式的绝唱。《陆小凤传奇》中的陆小凤、花满楼和西门吹雪是这样的,《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胡铁花是这样的,《欢乐英雄》中的郭大路、王动、林太平以及《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与阿飞也都是这样的。因此古龙不禁要赞叹道:“这世上只有友情存在就永远有光明。你看现在阳光正照遍大地,到处闪耀着金光,就好像上天特地为这世上懂得珍惜友情的人,撒下了片片黄金。”(《欢乐英雄》)谁就浪子无情,“大丈夫”心中自有令人振奋鼓舞的“真情”、“至情”。正如李寻欢所说:“有感情,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气,才有变化。”当然这种友情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获得的,因此 “大丈夫”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孤独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丈夫”之间的友情并非意识着可以互相纵容,也不能以友情的名义侵犯到人格的独立,损害尊严和自由。朋友之间也会互相指明缺点,互相帮助,但他会让朋友自己去解决而绝不越姐代危,一手包办,因为他同样尊重朋友的自主,相信朋友的能力。《七种武器》中高立到孔雀山庄求援,秋凤梧借给他孔雀翎,以激励高立,使他恢复了自信,最终战胜了强敌,而后来高立才知道这孔雀翎是假的,秋凤梧给他的是精神上的鼓舞,但这种帮助比越俎代庖、助拳驱敌更显亲切、高尚和可贵。而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却为报答龙啸云的恩情,竟将全部家产和恋人都送给人龙啸云,这种以怜悯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施行的帮助,实质上是对他人的侮辱,根本没有考虑到龙啸云的自尊和人格,因而最终酿成悲剧。幸亏阿飞还很清醒,他受到林仙儿的欺骗,而李寻欢非但不设法让他看清林仙儿的真面目,让他自定行止,却反而自以为很伟大地牺牲自己去求吕凤先,让吕背着阿飞去杀林仙儿,这时阿飞马上意识到 自主与尊严,警觉地责问:“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一定要左右我的思想,主宰我的命运?”只有这样交往的友情才是“大丈夫”那淡如
水的君子之交。
第三,追求自由。“大丈夫”人格同时也是自由的。这自由体现在他们那出自内心的行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自己内心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或世俗的伦理道德体系的规范,是“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⑨他很清楚身为“大丈夫”他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他通常有颗善良而真诚的心灵,愿意与他人分享快乐,他也爱管一些闲事,甚至不惜奔波千里去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伸冤报仇,仅仅因为他自己愿意这么做。而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哪怕要放火把他家烧光,甚至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去做的。因为他知道“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有些事明知不能做,还是非做不可。”(《楚留香传奇》)显示出“大丈夫”的率性而为。他做了许多仁义之事,但并不是为了遵循那些所谓的 “江湖道义”而完全是按照自己内心一贯的道德法则而行事,非迫于外而是感于内,是他自己真情实感的体现,所谓“为仁由己”。如 《欢乐英雄》中郭大路一听到 “棍子”杀人,马上跳起来 冲出去救人,快得连“侠应救人”这一念头都不曾起过。“大丈夫”做了侠义之事也并非要获得别人的感激,不为名也不为利,可说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为“大丈夫”是顶天立地、刚毅果敢,不屈从与任何权威或形式格律的,正如孟子所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⑩这里他所做的是自己愿意做并且觉得应该做的事,实则是一种“自律”的表现,他那看似随心所欲的行为并非盲目或偶然的,而是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正是从中体现出了 “大丈夫”人格的自由性。
那么为什么“大丈夫”出自内心自由选择的所做所为基本上都是符合“天道”的呢?这也是根源于“大丈夫”的孤独感。正因为他们的无依无靠,“大丈夫”就恰好能摆脱尘世间种种的外在束缚,处于一种 “无心无我”之境,如同道家所谓的“心斋”、“坐忘”的状态。“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夫询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11]“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2]以一种理性直观的方式用心灵来把握最广阔的天与地,与天地之大道相融通。从而“大丈夫”也就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性,从尘世上升到天上,以天地之大道作为其所作所为的内在原则和最后依据,将其内化为自己心中一贯的道德法则,由此天地也就成为了支撑他们的行为举止的背后力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天地大道通过他们而自然而然地呈现。于是“大丈夫”的潜意识里生发出一种高于世俗社会、高于常人的道德优越感,再又从天上回归到尘世,以高于现实社会的姿态来“替天行道”,进行仁义之举。
“大丈夫”人格也还体现在其它一些精神情感方面,如《七种武器》中所揭示的那样:《长生剑》写笑,《孔雀翎》写信心,《碧玉刀》写诚实,《多情环》写仇恨,《离别钩》写坚强的求生意志,《霸王枪》写爱,《拳头》写勇往直前的斗志。这些也都很有意义,在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论述了。
综上所述,古龙的 “大丈夫”理想人格(作道德意义解)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它以孤独感(以此为基础的重责任、重尊严)、重友情、追求自由为主要特征,其核心就在于独立平等、自由的主体人格(作个体意义解)。在这个基础上,包括自律、自信、自强,包括果敢、坚毅、聪颖、豁达、宽容、纯真、热爱生命与和平、对人类充满爱与信心等等,总之,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格理想,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感和自由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中贯穿着古龙反异化的思想。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激烈动荡的时期,前二十年的国民党政权体制受到动摇,暴露了台湾社会所潜藏的种种问题,价值观念崩溃,人们处于焦虑、失落之中。古龙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他不仅对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还立图树立一种理想的人格模式,以反抗社会对人的异化,恢复人的纯真的本性,重获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古龙要恢复实用理性之外的人的感性方面,重视人的精神情感的力量,讲求人性,将人从已堕落为单纯实用和实证的工具理性束缚中解脱出来。《绝代双骄》中的花无缺人如其名,出身于江湖上名声最响的武林圣地,少年英俊,谈吐高雅,不虑钱财,武功盖世,名声远扬,看似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小鱼儿去敏锐地指出,花无缺少了样东西——感情,他不曾尝过爱的滋味、恨的滋味,甚至连烦恼也没有,老、弱、病、残、愁闷、贫苦、失望、悲伤、羞辱、恼怒……这些本是人类都不能避免的痛苦他一样也没有,一个没有痛苦的人也同样不能真正领略到快乐的滋味。因为小鱼说:“别人也许羡慕你,我却觉得你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其次,古龙注意弘扬人性中那些美好的方面如爱、宽容、信心等而批判那些丑恶的方面如贪婪、自私等。在他的作品中,“大丈夫”的武功不是用来杀人而是用来救人的。武世盖世的楚留香、陆小凤等人行走江湖,出生人死,揭露了一个又一个的江湖阴谋,却似乎手上少有血腥。他们很少出手,万般无奈之下也不过点到即止,让人心服口服,其目的是将对手击败而不是要大开杀戒,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宽恕、仁爱之心,追求从精神、气势上压倒对手从斗志上瓦解对手,以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古龙还充分揭露了那些外在的功名利禄对人性的异化,如小鱼儿就认为那些所谓的“宝贝”拿来 “玩玩倒还好,但若要保留它,可就伤神了,又怕它丢,又怕它被偷,又怕它被抢,你说多麻烦。……听说世上有些人专门喜受聚集钱财,却又舍不得花,这些人想必是呆子。”因为 “世上所有的财宝也填不满一个人心里的空虚。”(《欢乐英雄》)在古龙看来有了欲望和财富,一个人也就很快会变的,正如醋会使水变酸一样。
再次,古龙也对封建的世俗礼教对人的束缚十分不满,认为这只会使人更虚伪,成天戴着假面具做人而不能以真面目率性而为,从而丧失了最可贵的个性。如古龙笔下的李寻欢就很注重忠恕之道,讲求克己复礼,他为了友情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昔 日恋人而宽恕了龙啸云的不义等等。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很崇高、很伟大、但实际却只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整日愁眉苦脸,抑郁寡欢,恰好证明了“仁”的虚伪性和不现实性(《多情剑客无情剑》)。于是在《萧十一郎》中一向对女性并不大重视的古龙甚至让深受封建礼俗异化的大家闺秀
沈璧君也实现了个性的觉醒。
此外,古龙还注意到生活在这种世俗的功利社会中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产生异化,“在江湖中混的人,本就是要互相欺骗,才能生存。”(《七种武器》)为了功名利禄,有人出卖自己,有人出卖了朋友,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多情剑客无情剑》中上官金虹为了利用荆无命,连后者杀了他的亲生儿子都不为所动。但这些到头来却是一场空。《萧十一郎》中那些人人称颂的连城璧等所谓的 “侠义之士”的出身名门,温儒谦让,一言一行看似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耻的小人,为了自己的贪欲和权力欲巧设陷阱,陷害他人。而被人人视之为无恶不作的大盗萧十一郎,却是一位行侠仗义、一身清白,只靠自己劳力谋生的真正的“大丈夫”。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无怪萧十一郎常凄凉而悲枪地吟唱 “暮春三月,草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伺狼?人皆怜羊,狼独悲枪,天心难测,世情如霜!”感叹道:“狼只在饥饿难耐,万不得己时,才会吃自己的同类,但人吃得很饱时,也会自相残杀。”尽管如此,古龙也仍执著地相信“人也有忠实的,也有可爱的,而且善良的人永远比恶人多。” (《萧十一郎》)他始终认为“一个人和一只食尸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有区别的。”(《大地飞鹰》)他希望人与人能够以诚相待,以心换心,建立一种真挚的情感关系。“世上最难得的,既不是名声也不是财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欢乐英雄》)
实际上古龙所向往的就是一种 “本真”的境界:人是 “本真”的人,社会是 “本真”的社会,没有虚伪,没有欺诈,不受名利礼教的束缚,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信心、决心和爱心去换取自由、爱情和快乐,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在古龙看来,这种生活并不是建立在外界物质财富的多寡上而是建立在健全的心灵之中,生命的过程在于每个人对生命的感觉以及由此衍生的做法。《欢乐英雄》中的郭大路等四人尽管生活在贫困、艰难的环境之中,如何解决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他们,但他们能够明白上述道理,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快乐地活着。而《陆小凤传奇》中的花满楼尽管是个瞎子,但却由于有一颗明亮的心灵,有一种温柔博爱的情怀,因此他听见过雪花飘落在屋顶的声音,能感受到花蕾在春风中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知道秋风常常带着种从远山上传过来的木叶清香,因此他比许多不瞎的人都要开心。他很满足,感激上天赐给他如此美妙的生命,能让他享受如此美妙的人生。这不正是庄子所推崇的能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13]的 “畸人”么?这种人生境界不正是令多少人向往和追求的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么?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作家必定是对于人的本质、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时代精神有着自己独到而准确地把握的,古龙也不例外。他将自己对当代异化了的人类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与问题所作的思考通过武侠小说这一形式反映出来,并试图将他的解决方法通过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他的 “大丈夫”人格理想来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正是古龙的武侠小说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共鸣,因而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从中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位通俗小说家而仍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注释:
① 参见《天涯·明月·刀》、《楚留香》等书序言
② 参见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5页。
③《孟子·告子下》
④⑤⑥⑧ 分别见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88、
113、134页。
⑦⑩《孟子·离委下》
⑨《荀子·解蔽》
[11]《庄子·大宗师》
[12]《老子》四十一章
[13]《庄子·天下篇》
主要参考书目:
古龙:《古龙全集》,海南出版社。费勇、钟晓毅:《古龙传奇》,广东人民出版,1994年版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欧阳莹之:《泛论古龙的武侠小说》,见《猎鹰·赌局》附录
陈墨:《古龙论》,见《古龙传奇)附录
陆灏、张文江、裘小龙:《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张缮:《孤泊天涯路,谁明浪子心——论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1期
刘贤汉:《古龙武侠小说散论》,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